当负面舆论困扰着国内的游戏市场时,我们往往会想当然的,钦羡于欧美、日本那些成熟开明的行业环境。但令人意外的是,来自北欧的从业者彼得·吕贝克(Peter Lübeck),似乎也对「舆论的阻挠」感同身受:「在瑞典也是这样……游戏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行业,很多人自己从来没有玩过游戏。」
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,他正在经营名为 Game Habitat 的开发社区。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,他们旗下有着北欧最大的游戏开发中心 DevHub,业务遍历独立游戏、3A 游戏,以及中间件和发行等各个领域。即使到了今天,吕贝克依然得努力的引导公众,以加深人们对游戏的理解。
![]()
彼得·吕贝克,Game Habitat 首席执行官
他的苦恼并非无迹可寻,「战争」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打响了。当时瑞典儿童环境委员会的代表玛格丽特·佩尔松(Margaretha Persson),将 Commodore 64 上的《最后的忍者 2》指明为暴力内容,她的主张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,与那时瑞典街头兴起的涂鸦文化被一并声讨,最终使得零售商不得不移除包装内附赠的塑料手里剑。
到了 1997 年,教科文组织委托北欧共同体成立了一个国际交流中心,以便向当地分发关于儿童、青年和传播媒介暴力问题研究的资料。这家机构想通过这种方式,加深民众对电影和游戏里暴力行为的认知。用瑞典人的话来讲,时至今日你仍能看到「愤怒的妈妈」时不时的出现。
![]()
《最后的忍者2》中的手里剑(图右下角)在瑞典被移除了
但成熟产业的力量却不可小觑,由于游戏是瑞典政府相当重要的税收来源,它自然而然的获得了一部分从政人士的欢迎。于是,政客瑞卡德·诺丁(Rickard Nordin)每周都会直播《炉石传说》,恰恰是为了迎合自己的支持者,有几个政党还在 2014 年大选时组织了场《星际争霸》比赛。
这背后蕴藏的力量,某种程度上帮助瑞典游戏产业冲破了枷锁,使得这个国家很快成为欧洲最为重要的游戏发源地之一,比肩英国和近几年发迹的波兰。EA DICE 和 Ubi Massive 自不必说,《逃出生天》和 Mojang 旗下的《我的世界》同样如雷贯耳,King 则在社交游戏领域独树一帜。
不过,那些瑞典开发者的履历,对我们而言又是否会有参考价值呢?
Demo-Scene:破解文化的升华
得益于经济自由、教育普及,以及丰厚的自然资源。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,瑞典就成了典型的「福利国家」,有着被穷人们誉为「从摇篮到坟墓」的服务政策。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来看,瑞典的福利开支超过总 GDP 的五分之一,使得公民的贫困比例始终被控制在 10% 以下。这一背景,很快就辐射到计算机设施的基础建设上。
有许多不同因素促成了瑞典游戏产业的成功。瑞典早在 90 年代就把宽带的发展放在了首位,当时有一项由政府资助的 Home-PC 计划,人们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购买家用电脑。
吕贝克口中的 Home-PC 计划,其实包含了两层面含义。一方面,自 1998 年到 2000 年,瑞典政府便向各地家庭交付了 85 万台设备,只要是那些育有子女的家长,都可以领着孩子从商店里买到廉价电脑。另一方面,由于不少公司得到了政府资助,企业雇员同样能够享受到「以税前价格入手电脑」的优惠。
可想而知,宽带的提前铺设,很快就与计算机普及率的迅速提高产生了化学反应,这在游戏产业生态的早期塑形中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作为佐证,根据《瑞典游戏开发者索引》的调研来看,在 2016~2017 年之间,63% 的瑞典开发者仍然将精力集中于 PC 平台,相较之下家用机只占到了 19% 的份额。
![]()
瑞典开发者更倾向于 PC 平台
但有趣的是,瑞典开发者的骨子里又有一丝与众不同的基因,如果说 Home-PC 是当地游戏市场发展的硬件基础,那 70~80 年代兴起的 Demo-Scene 运动,则奠定了整个行业的文化基础。
凛冬将至,对于吕贝克而言不完全是一句玩笑。到了 12 月尾声,当地日照时间将缩短到只有 6 个小时。2016 年时,斯德哥尔摩迎来了百年一次的大雪,出租车和巴士陷入瘫痪,地面列车也只能缩减班次。人们顶着雨雪上学、上班,还得在零下十来度的低温中去超市买菜。
![]()
2016 年的斯德哥尔摩大雪,人们穿着滑雪工具上班
在自然环境的逼迫下,瑞典人早早练就了一身「宅气」,除非很有必要,否则出门是一件性价比不高的事情。但由于身后有着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,人们总会最大限度的去「做一些想做的事情」。
漫漫长夜之中,孩子们从小学会在炉灶边取暖,听老人们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。而到了游戏开发者的场合,他们则借着安静的环境冥想出一个个创意 —— Demo-Scene 便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体现。
Demo-Scene 包含软盘、共享游戏和早期的互联网实验,起源于为了分享游戏而打破版权保护(的意图),但最终却导致人们开始制作自己的作品。
据吕贝克回忆,瑞典早期的游戏工作室大多参与了这项「破解运动」,DICE、Remedy 和 IO Interactive 的发迹均受其影响。具体来说,它的精神内核,是鼓励开发者探寻硬件的极限,在充满限制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制作高质量软件。
但最初的理念其实与盗版无异,即在被破解的软件界面留下「水印」,宣传自己或者团队的名字。人们后来渐渐不满足于纯文本水印,开始在其中加入动画和音乐,久而久之,这就成为了开发者炫技的一种方式。
![]()
瑞典人做的 Demo-Scene
硬核到什么程度呢?比如通过 Amiga 电脑,看看谁能在每帧画面上展示足够多的「Bobs」(可以理解为图形元素),或者是对比 Commodore 64 上滚动字节的数量。甚至连雅达利都招安了一些人,帮自己制作带有视觉效果和音乐的循环演示,以便于 Atari 400/800 电脑能够吸引更多的商店顾客。
用「垃圾设备」开发「高端内容」的风潮,显然为瑞典积累了一大批游戏人才。成立于 1992 年的 DICE,前身便是维克舍大学的 Demo-Scene 团队。小组成员当时在一间宿舍内办公,期间为 Amiga 平台制作了《Pinball Dreams》《Pinball Fantasies》等数款弹珠游戏。此时又恰逢 Home-PC 政策开始推行,两者合力之下,这家公司才得以平稳的发展。
「白嫖」的教育,反而是最好的教育
事实上,大部分瑞典游戏公司都有着不错的财务状况。2016 年,瑞典游戏行业的总收入大约有 25% 来自中小型企业和独立制作人。虽然 THQ Nordic 和雪崩工作室近两年发展较为迅速,大企业的收入占比有了一定提升,但中小型企业仍然占到了 20%,这意味着很多开发者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。
坐落在马尔默的 Tarsier Studios,曾经制作了脍炙人口的《小小大星球》和《小小噩梦》。Mediocre Games 的成员只有两个人,在全球却拥揽 3 亿名用户。吕贝克认为这可以追溯到当地游戏产业成功的最初原因,受益于社会保障制度,人们有机会冒险,进而去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。
![]()
《小小噩梦》
免费课程显然是保障制度的其中一环,瑞典有许多不收取学费的职业技术大学(Vocational University),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 Game Assembly,它已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游戏教育机构之一,背后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高级职业教育项目。
游戏职业技术大学的课程一般为 2.5 年,一半时间用来集中教学,一半时间主张个体发展,培养对象则包括艺术家、程序员、关卡设计和动画师。到了最后的 6 个月,学生们会被分配到不同的游戏工作室实习,实习结束基本宣告转正。在 Game Assembly,超过 90% 的人毕业后直接找到了对口工作。
![]()
Game Assembly 提供的学生活动室
类似的学校,还有位于瑞典法伦的 Playground Squad。但值得一提的是,并不是路边随便来个老大爷就能直接入读,人们需要提前提交申请。Playground Squad 就会审核申请人的能力和作品,通过率往往不到 10%。由于非北欧地区的招生占比低于 20%,对外的竞争非常激烈。
为了打好基础,对游戏怀有志向的年轻人,也可以先去舍夫德大学这样的全日制学校就读。从 Home-PC 的时代开始,舍夫德大学就加速了计算机设施的铺设,到 2002 年便有了自己的游戏专业。他们主张拓展知识覆盖面,把程序、艺术和设计方向的学生混起来,一开始就让人们相互学习。
![]()
舍夫德大学的学生相当少,只有 3500 人
而与免费教育紧密对接的,则是瑞典的非营利型孵化器,吕贝克经营的 Game Habitat 正是其中之一。它由南部的游戏公司发起,目标是围绕马尔默建立一个产业枢纽中心,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和工作室入驻,鼓励开发者创业。瑞典的税收额度相当高,游戏公司的贡献不菲,这导致马尔默政客对游戏的态度十分友善,孵化器往往会得到国家层面的援助。
「Game Habitat 由当地政府(马尔默市/斯科讷地区)和游戏产业成员资助,我们主要受到他们的支持。但我们确实与其它中心合作,比如位于舍夫德的 Sweden Game Arena,位于北部的 Arctic Game Lab 和位于卡尔斯港的 GamePort。」
![]()
Game Habitat 提供的独立办公室
吕贝克提到的「产业成员资助」,大致指的是企业缴纳的会员费,会员可以象征性的获得一些独家活动和展示机会,最低收费为一年 3000 瑞典克朗(2100 元)。当然这并非是强制性的,非会员仍然能以低价租到 DevHub 的办公场所,比如二楼的共享办公室和休息室一个月只需 1400 瑞典克朗(1000 元),相当于北京一间隔断房的租金。
受制于人的甜蜜烦恼
但在如此令人钦羡的环境下,瑞典开发者也有自己的烦恼。打个比方,当你听到《战地 5》和《全境封锁 2》时,第一反应是它们出自美国和法国。尽管开发商 DICE 和 Massive 赫赫有名,这两家公司也没有那么强的「瑞典属性」,优秀工作室成了海外资本觊觎的对象。DICE 被 EA 收购,Massive 处在育碧麾下,Mojang 被微软纳入囊中。
瑞典的识字率达到 99%,当地语言是源自于古诺尔斯语的北日耳曼语,然而受到北美文化的影响,他们却天然的对英语没有阅读障碍。站在吕贝克的角度来看,这也是未能形成自我特色的一个侧写:
很少有东西能脱颖而出,瑞典人对西方、尤其是流行文化的理解,建立在大量美国媒体、电影和电视剧从小陪伴的基础上。所以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握英语……到目前为止,工作室被海外企业收购还没有对行业造成太大影响,因为国际发行商允许他们继续做最擅长的事情。我不知道长期来看会有什么问题,但希望更多(瑞典)企业能够独立自主,而不是卖给外国公司。
虽然瑞典仍然涌现了一批偏向本土文化的作品,比如 Simogo 的解谜游戏《Year Walk》,就深植民间传说,它展现了北欧人对于神话的悲观情绪。而《突变元年》和《零世代》的后启示录故事,也发生在末世之后的瑞典。但从整体来看,它们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。
![]()
《Year Walk》的氛围十分压抑
至于游戏发行工作,因为税金不低,再加上高昂的人力成本,相关业务显得不那么受欢迎。作为参考,在 2002 年之前,瑞典出版业的增值税达到 25%,后来为了保证图书多样性,政府才将数值下调到了 6%。Paradox 和 THQ Nordic 算是两家还算靠谱的瑞典中型发行商,Starbreeze 早已是江河日下,其它能说得上名字的就没有多少了。
![]()
THQ 这个品牌,算是被瑞典厂商 Nordic 给救了
另一个「甜蜜的烦恼」,源于游戏人才的缺口。吕贝克表示,尽管教育体制竭尽全力为这个行业提供人才,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从世界各地招募员工,以跟上增长的步伐,超过三分之一的瑞典游戏从业者是来自其它国家的移民,这与雪崩工作室首席人力资源官威尔逊的口径一致:
行业正在迅猛增长,而且速度之快,已经超出了我们培训开发人员的速度。公司通常采取的措施是从国外招募员工……雪崩工作室大约有 35% 的员工移居瑞典。
但不是所有的海外人才都愿意移居瑞典,大多数游戏公司集中在斯德哥尔摩,这里的住房成本接近英国伦敦(便宜的房子大概 300 万元一套)。复杂的签证也是个麻烦,非欧盟工人每隔几年就得更新一次许可证,若是雇主搞不清那些官僚化的流程,很可能导致员工被遣返回原籍国。某种程度上,这或许也是瑞典游戏产业努力推行平等工作环境的原因,自 2012 年到 2017 年,女性从业者的增长速度(255%)远大于男性(157%)。
![]()
马尔默
近年来的情况倒是有了些许改观,如果你想在瑞典从事游戏开发工作,斯德哥尔摩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了。Game Habitat 所在的马尔默发展稳定,Arctic game Lab 也开始在人烟稀少的瑞典北部倡议创建和培育一个战略平台,至少那些海外人才有了更宽松的选择。
而通过这些论述,相信一个稍显模糊,但又环环相扣的产业图景已经呈现于前。政府、教育机构、孵化器,个人与企业形成闭环,无论从利益还是道德的层面出发,他们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一切似乎都建立在长远考虑的目光之上,也许抛开某些纠葛,这才是游戏行业理应展现的健康面貌。
(编注:感谢 Game Habitat 协助本次采访。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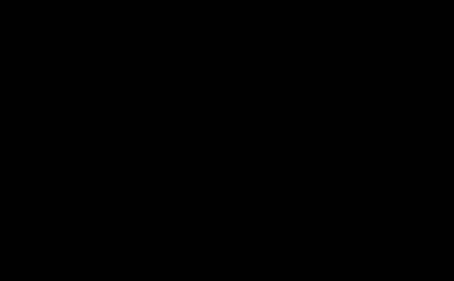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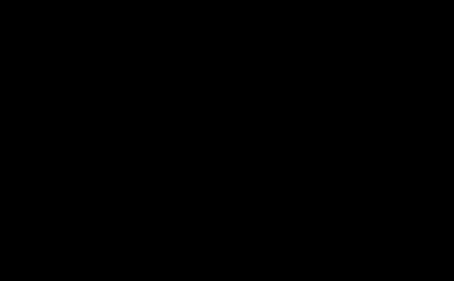
回复
北欧的福利羡慕不来,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。
回复
用户越少的游戏新闻平台,质量普遍越高诶
回复
小小噩梦超级棒